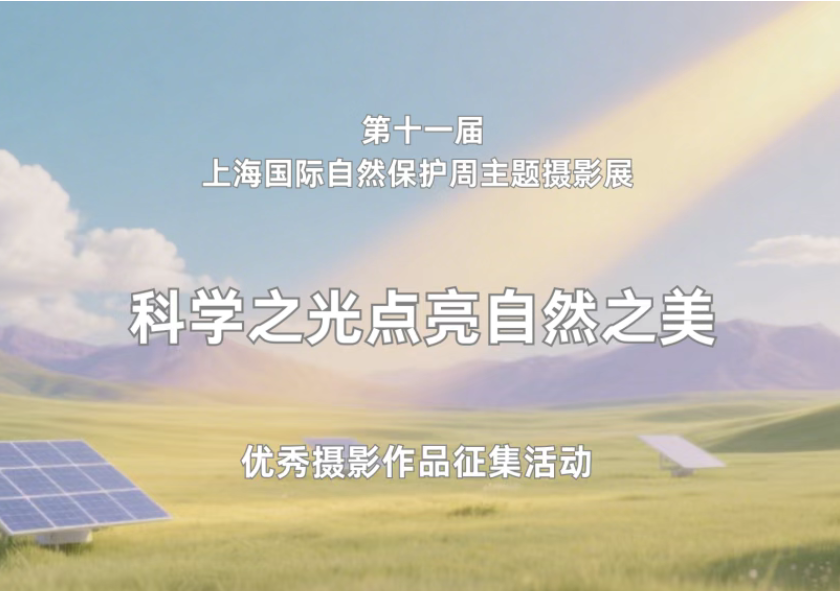我是一个医生,以治病救人为业。在医疗实践中深感让病人也了解一些医学知识的重要性,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很好地配合医疗,取得较好的医疗效果。因此我在诊病的过程中常常会向病人做些关于病情及医疗措施的解释,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给病人做些医学科普的工作。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国家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科学技术的普及,一些报刊杂志都开设了有关医学科普的栏目,我在临床医疗工作之余,也积极给这些栏目投稿,我觉得这样科普工作的受众面会更广。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时也开播科技节目,其中有一个关于医药卫生的栏目,名称叫做“医药顾问”。记得最初这档节目每周以同一内容播出3次、每次20分钟。编辑组人员到各大医院找医务人员讨论节目内容,並商请医务人员来电台录音,编辑整理后定稿播放。
1984年初他们曾邀请中山医院4位医生来电台录制节目,其中便包括我。给我的讲题是:生了癌究竟能不能吃鸡?这是一个民众十分关心的话题,很接地气,我在门诊工作中也常常被问到,所以我也很有兴趣解答这个问题。我还为此查了《本草纲目》,其中便提到鸡肉性味甘平,补中益气,填髓生精,乃大补之物。癌症的病人大多身体虚弱,按中医的说法是虚则补之,因此,应该可以吃鸡。至于民间有鸡容易生癌的说法,我说我曾在江苏某地做肝癌的调查,便发现该地有鸭子生肝癌,但却没有鸡生肝癌的。当然,如果所服中药或有某些特定的治疗与之抵触,可能不宜,但不是所有的癌症病人都不能吃鸡。鸡的营养丰富,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病人的免疫力,对抗癌有很大的好处…… 据说播出之后听众的反应甚好。
过了一两个月以后的一天,电台科技节目组的一位姓金的女士来找我,说是她们台里希望我能去帮助她们主持“医药顾问”节目,並已经征得中山医院领导的同意云云。我当时也没多考虑,只是担心别花费我过多的时间就好。金女士说得轻松,说是我专业熟悉、语言流畅,录一档20分钟的节目,至多花半个小时,一个月用4档节目,只需去电台录音间半天便可完成。就这样我被他们“噱”了去当上了他们所称的 “嘉宾主持”。
1984年4月1日由我作嘉宾主持播讲的医药顾问节目正式开播,记得那天的讲题是“什么是澳(大利亚) 抗(原)“,澳抗是当时对乙肝表面抗原(即HBsAg)的称呼,民间对此有许多误解,我觉得很有必要 ”科普、科普“。这个讲题是我建议的,台里各位领导也觉得挺好,后来他们便索性由我来决定讲题了。他们交给我许多听众来信,有的提出希望了解某个方面问题的,有的直接询问怎么治病的等等,我便在其中选择有共性的、适于在电台播讲的话题,事先报给他们备案,他们都会尊重我的选择,偶尔也会建议我考虑讲什么话题。我是一名内科医师,主要从事肝癌的医疗及研究工作,所以一般内科、肿瘤等专业的话题,我事先略作准备,大致也都能顺利播讲,但是妇产科、五官科、口腔科等专业性很強的内容,我觉得请专科医师讲更好,节目编辑组便将此事委托于我,由我邀请相关专家主讲,而我则在节目中担任主持人的角色,作些引导、解释、強调之类的说辞,以保证节目内容的准确和通俗易懂,到是真正成了“嘉宾主持”了。

在电台录音室录制 “医药顾问”节目
据说,广播电台邀请专业人士以嘉宾的身份主持节目,是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医药顾问节目首开先河的。这也说明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广播电台领导思想的解放吧。
后来我担任了中山医院的副院长,除了临床医疗工作以外,又多了医院管理的工作,有时确实感到忙不过来,便建议电台领导再请一位“嘉宾主持”,我们可以交替主持,以便确保节目按时录制、播出。结果很有趣,他们请到的另一位嘉宾主持却也是一位忙人:仁济医院的副院长朱明德教授,朱教授是肾脏内科专家,我们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在电台科技节目编辑组贺钖亷、金毓褆等同志的指导下,十分默契地做着这一份对我们来说都是份外的工作。
对于这份“份外的”工作,我也是很认真地对待的,记得80年代中期我曾应英国皇家学会之邀赴英国考察,考察将近结束时,接待方询问
“还想看看什么?” 我便提出去看看BBC(英国国家广播中心)的科学广播,结果他们还真的安排了。BBC 的科学广播中也有医学节目、当时的主持人名叫戴维,一位约40来岁的男性白人 ,当天的讲题是“黑色素瘤的新疗法” ,讲稿是戴维写的,但他不是医生,他去釆访了医生,还录了一段医生的话,以示可信,一并交给播音人员播出了。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请这医生来讲?他说
“他们哪有这空”。回国后我讲给电台的编辑们听,大家都笑了。
40年前通讯手段不像如今之发达,除了阅读报刊杂志以外,看电视和收听广播是许多民众主要的信息来源,也是他们获取一些科学知识的主要途径。播讲医药卫生知识的
“医药顾问”节目关系着民众的健康,更是收听率名列前茅的节目之一。为响应听众的需求、适应广播事业的发展,我们主持的节目也在发展,播出的内容和频度都在增加,后来随着虹桥路广播大厦的建成,上海广播电台迁入新址,录播的
“医药顾问” 节目也发展成了直播的 “名医坐堂”了。
“名医坐堂”是一档直播节目,主讲人讲完后听众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并要求当场给予解答。这样一来对于主持人和主讲人的要求都明显提高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名医坐堂节目是安排在每周日的下午1:00~2:00的时间里。周日本是休息日,下午1:00~2:00又是午餐后的休息时间。休息日里的休息时间,正是广播的“黄金时间段”,因为这时应该是听众最能心无旁骛地听广播的时间,事实也确实是如此,一些老听众们常常在午饭以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收听名医坐堂节目,并争取打进电话,咨询健康问题。节目播出时,咨询电话常常爆满,一些多次打不进电话的听众还会抱怨。编辑人员只好记下他们的来电号码,答应他们在节目结束后请主持人给予他们个别解答。

在电台直播主持“名医坐堂”节目
朱明德教授和我当时虽然都已经分别担任了上海仁济与中山两家大型
“三甲”医院的院长,但我们也都仍然与其他医师一样,还做着临床医疗、教学与科研的工作,即是俗称的“双肩挑”吧。电台的 “嘉宾主持”工作我们一直坚持承担下来,确实是出于对医学科普工作的一种责任感。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治病救人,促进人们的健康是我们的应尽之责。在医院里给人治病是我们的责任,在电台做医学科普节目,也同样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电台的这项工作虽然多年来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我们无怨无悔。
支撑着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还有听众对我们的期盼和信赖。记得在1996底吧上海广播电台曾经在科学会堂为我举办过一个“名医坐堂节目顾问聘请仪式” ,我又多了一个顾问的名义。会上有领导对我作了嘉勉,但是更令我感动的是电台科技项目编辑组的同志们,他们一直是这个节目的幕后英雄,他们追访到一位老听众,这位老同志每次收听我所主持的节目时,都做了详细的笔记,会上他展示了他的收听记录竟有10来本之多,真是令人感动。
一位素未谋面的工人同志给我写信,说一天他在十六铺轮船码头候船准备回乡时,在候船室里听到我在广播里面讲到大便出血不一定都是痔疮引起的,应该就医检查,以免遗漏直肠癌的可能性。这位工人说他当时正有大便出血的问题,于是退掉了船票,到医院检查,果然是直肠癌出血。随即住院做了手术切除,幸而还在早期,得到了根治,是我们的节目救于他一命。
一位当时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大二年级的学生写信给我说:她家的老人都喜欢收听我们的医药节目,她也喜欢上了医学,高中毕业后她考进了第二医科大学,希望以后像老师一样一面做医生给人看病,一面宣传医学知识,让人少生病、不生病。
一次我乘出租车回中山医院,这位司机对人的口音很注意,竟然从我不甚标准的普通话中、听出我大约就是在电台讲医学知识的中山医院杨医生,原来出租车司机在接送客人的间歇、很多时间都是在听广播的,对我的声音竟是十分熟悉,于是说起“你们真是做了一件关心民众的大好事情”。车到目的地,他竟表示要我 “免单“了 。车资当然最后还是付了的,真是让我感动不已,一个人为人民大众那怕只做了一点好事,民众也都是认可的。
到了2000年前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民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名医坐堂节目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博釆众长,又聘请了包括中医、儿科等领域的好几位专家加入“嘉宾主持“的队伍,这些同道们年轻有为,干劲十足,节目越办越红火了,我与朱教授也就逐步减少了参与。
大约到2003年以后,我便完全离开了名医坐堂节目,算来前后也有将近20年的时光。感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个舞台上为民众健康做了一些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
名医坐堂节目如今仍在继续,祝它越办越好。
原载:《上海滩》2024.7.P12
作者与公众号简介
本文作者杨秉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复旦大学中山医院院长、上海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等职,因肝癌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项。
本公众号名为:“”主要发表作者本人原创之医学科普作品及小说、游记、随笔、图画等文艺作品,敬请关注,欢迎批评指正。